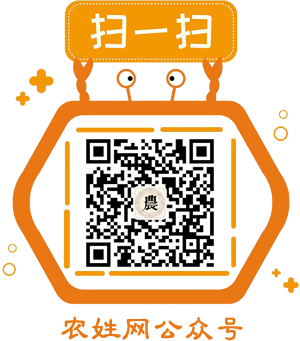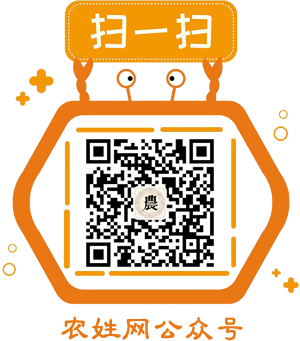
评农安业荒唐言论
农安业打着“广西农(侬)氏族谱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讨组”旗号,以“用正确的视角看待农氏历史,增强天下农(侬)氏族是一家意识”为题撰文网传(以下简称“该文”)。该文从标题到内容,全凭个人想象杜撰而成,无事实,无根据,是十足的歪理邪说,自我吹嘘,徒有虚名而已。
农安业到处鼓吹:农是“贱”意,农姓是“农奴“,“侬氏是农氏灵魂”,“农改侬是先进思想文化意识”,“历史上本来就是大侬小农”等等。这就是他所谓“用正确视角看待农氏历史”,“农、侬一家”,只有在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,或者是农、侬家族亲如一家的共识下才成为事实。作为家族,农、侬各有不同源流史,不同的迁徙落籍,繁衍生息过程,不可能是“一家”。何来“天下农侬一家意识”?
该文大概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了吧?文如其人,通篇充斥着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史观。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,不懂装懂,胡编乱造,无中生有,自欺欺人。对史书记载,他不敢正视,对失实的所谓老族谱,他如获至宝,以讹传讹,对他人的正确见解,他从对中求不对,对自己的错误观点,则从不对中求对。说他是赵树理先生笔下的“常有理”,虽嫌过于包容,但却也有几分相似。对这种人论理,犹如对牛弹琴,但为了激浊扬清,还农氏家族一个风清气静生态环境,故对其种种谬论仍有澄清的必要。
不懂族史 妄论族史
农安业说:“农侬有别,大概也是十多年前的事”。只有不懂中华姓氏史,不懂农、侬两个家族历史和现状的人,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中华姓氏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,在无文字时代,便以物化图腾为标志,作为氏族之间的“有别”,才能实行“远禽兽,别婚姻”的族外婚姻。自从有了文字之后,文字姓氏逐步取代氏族图腾,成为“有别”于其他家族的标志。农氏家族诞生于周代,从诞生之时起,就以“农”为标志,“有别”于其他家族。侬氏诞生于唐代中期,同样从诞生之时起,以“侬”为标志,“有别”于其他家族。农氏比侬氏早诞生1300多年,这一千多年只有农姓,无侬姓,无所谓是“有别”或“无别”,但总不能说农、侬是“一家”吧?自唐之后,有了侬氏,农、侬是否就是“无别”,就是“一家”了呢?《新唐书》卷222《南蛮传》如是说:“西原蛮居广容之南,邕桂之西……黄氏、周氏、韦氏、侬氏相为唇齿”。黄、韦、周、侬同居一隅,相为唇齿,尚且不属一家。农氏祖先是外来的,非西原州原住民,何故倒成了“农、侬一家”?不仅无事实依据,逻辑推理也站不住脚。和中华千万个家族一样,农、侬“有别”,从各自诞生之时起,已分别有几千年,一千多年历史,绝不是“十多年前的事”。如果说十多年前,在农、侬两个家族中发生了什么,那就是有人不顾氏族学原理,不顾农、侬两个家族历史和现状,抛出“农、侬一家”的错误观点而遭到广大族人抵制。如今农安业接过祖师爷衣缽,甚至走得更远,其处境恐怕比他的前人更不如意!
用侬猷替代炎帝 颠覆农氏祖宗
农安业说:“出自雁门的雁门农,才是我们广西农氏真正最高祖宗,也就是说侬智高爷爷侬猷才是我们广西雁门农最高祖宗”。
必须申明,天下农氏是一家,广西农氏家族是宗族大家庭的一部分。有共同祖先,共同发祥地,共同姓氏来源,共同堂号。农安业开口闭口“广西农氏”,这是妄图肢解农氏家族,将广西农氏与宗族大家庭分割开来的卑劣行径。其险恶用心值得警惕。
昔日赵高指鹿为马,当今农安业以侬猷替代炎帝为农氏家族最高祖宗。时代不同,对象不同,但性质相同,都是以假充真。历史上有朝代更替,有改名换姓,但更换祖先闻所未闻。农安业用侬猷替换炎帝作为农氏家族最高祖宗,可谓开了历史先河。
侬猷何许人?名不见经传。农安业是从一本被其称为“正确历史”的《全国侬姓族谱》(注:该谱因严重失实,农姓族务委员会在1996年编纂《雁门农氏宗族谱》时,经族委会讨论否定)中“研究”出来的,然而该谱並无侬猷其人。侬猷出现在1936年,由两位农氏族人编写的《农氏族谱》中(注:该谱同样严重失实,农姓族务委员会在1996年编纂《雁门农氏宗族谱》时,经族委会讨论否定)。他们所说的这个侬猷的真伪姑且不论,就其所描述的侬猷祖籍为湖南省长沙府茶埠县,于唐代在当地做了63年州官,享年84岁。与农安业说的“正宗雁门出身,从雁门到山东,又从山东一路走到广西左江,融入当地人,形成强盛的侬峒侬族”的侬猷,显然不是同一个人。然而应该肯定的是:作为“农氏最高祖宗”的侬猷,至少与农氏家族同一时代的周代人(注:周代分西周—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770年;东周—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5年)。而侬姓诞生于唐代,岂不是先有侬猷后有侬姓,这不就颠倒历史,颠倒逻辑了吗?更匪夷所思的是,农安业封给侬猷两个头衔,一个是“农氏最高祖宗”,一个是“侬智高爷爷”。农氏诞生于周代,侬智高出生于宋天圣三年(1025年)。从周至宋天圣年间至少相距约1500余年。也就是说,爷爷比孙仔大1500余岁,这是古今中外仅有的奇闻。话说到这里,侬猷是个什么样的人,应该明白了吧?侬猷不是凡人,凡人哪能话到一千五百多岁?是神仙,是农安业制造出来的神仙。农安业可以制造神仙,但绝不能以任何人代替农氏祖先。
农安业还说:“炎帝姓姜,非姓农,怎能拿来当农氏始祖呢”?炎帝姓姜,非姓农,尽人皆知,而作为农氏共同祖先,有理有据,有史可循,农安业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,足见其知识肤浅。
相传炎帝出生地在今陕西省岐山,武功一带的姜水流域,随着历史的进程,其势力逐渐向外扩展到河南,河北,山西,甘肃,山东,湖北,安徽以及岭南一带。随着势力的扩大,姓氏也相应得到发展,仅姜姓一支就占有16个地方,发展成为247个姓氏,全国许多著名姓氏如,许,谢,高,崔,沈,焦等都由姜姓发展而来;历史上炎帝是部落联盟首领,诸如祝融、共工、四岳等氏族都是其成员,这些不同氏族,虽各有不同血统,不同发源地,但都认同为炎帝族系,当他们的后人,寻根问祖时,自然也就寻到炎帝为“根”,有这样一个例子:共工氏后人为了纪念他,便以“共”为姓,相传共工氏善于治水,又有人以与他的职业相关为姓,取姓“洪”,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句龙,句龙后人就把龙和共结合在一起,取姓“龚”。共,洪,龚,都不是姓姜,但都是共工氏后人,而共工氏是炎帝部落联盟所属,因此,追根溯源都认同炎帝是自己祖先。其实,在中华姓氏历史上,由于各种不同际遇,以异姓为家族祖先并不少见。如黄姓始祖是颛顼,陈姓始祖是舜,林姓始祖是比干,覃姓始祖是伯益等等。历史上的炎帝有庞大的族系,非姓姜的家族,认同其为祖先又有什么奇怪呢?
炎帝神农氏之所以是农氏家族共同祖先,最根本的原因是炎帝是农氏的得姓始祖,农姓来源与炎帝有直接关系。
农氏主要姓源有二:一是以父、祖号为姓。炎帝号神农,后人便以农为姓,《国语·鲁语上》云:“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,其子曰柱:能植百谷百蔬。”《礼记·祭法》则称:“厉山氏有天下也,其子曰农,能植百谷”。其后人便以农为姓;二是以官为姓。西周初年,周武王封神农氏后人入朝为农正官,司掌农业丰稔祈祷诸事,后人便以农正官的“农”为姓。
姓氏来源亦即是家族的起源,无庸置疑,炎帝神农氏是农氏家族的始祖。《山海经》收录炎帝神农后裔36个姓氏,排列第25位是农姓。至于农姓与姜姓的关系,由公安部门以户籍为根据的姓氏人口调查确认:“农姓主要源于姜姓”。这不仅更明确农氏的来历,也给“农侬一家”当头一棒。东汉应劭在其名著《风俗通》中云:“农,神农氏之后”。难道他不知道炎帝是姓姜,非姓农?由几十名大学士编撰的清《康熙字典》,也确认:“农,神农氏之后”,难道他们也不知道炎帝姓姜,非姓农?当代诸多姓氏专家学者都无例外地确认,农,是神农氏之后,难道他们也都不知道炎帝姓姜,非姓农?直到今天才被农安业“研究”发现这个“旷世秘密”?农氏家族几千年来,认祖归宗,难道就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祖先?直到今天由农安业找来活了1500多岁的侬猷,才有自己的“最高祖宗”?别耍小聪明了。不知为不知,知也;不知为知之,蠢也。农氏族人只认炎帝神农氏为自己祖先。侬猷是那家“最高祖宗”?谁认由谁拜,与农氏家族无关。
农安业又说:“炎帝不是在雁门出生,把神农作为农氏最高祖宗,又掛雁门堂,是不伦不类的做法,还让人笑掉大牙”。不懂农氏家族历史的人,只能讲有悖历史的话。炎帝是农氏家族的得姓始祖,是农氏家族的“根”。雁门,是农氏家族的发祥地。对农氏家族而言,炎帝和雁门是“根”和“源”的关系,是先祖与后人的关系。在雁门繁衍生息的农氏族人是炎帝的后裔。正如《百家姓谱·姓氏图考》所载:“周郡之制始,因怀炎帝神农氏之德,雁门郡仅限农姓一族…”,农氏族人永远铭记祖德祖恩,只有数典忘祖的人,才否定这一铁的历史事实。历经沧桑,随着雁门农扩枝散叶,如今农氏族人,遍布中华版图各方,乃至世界各地,情况变了,但永远不变的是,他(她)们永远是炎帝神农氏后人。名作家冠品族亲说得好:“若从炎帝算起,农氏的血脉,就象主动脉分成无数支脉,支脉又紧连着主动脉跳动与流动着,共同维护这一健康的氏族躯体”。
标志家族的地域和血缘所出的“雁门堂”,是农氏家族的堂号,凡是农氏人家,不论远近亲疏,也不管走到天涯海角,掛“雁门堂”,天经地义,名正言顺,只有不懂得农氏家族历史渊源,不伦不类的人,才会说出如此不伦不类的话,被人笑掉大牙的正是他自己。
处心积虑 伪造侬智高家史
侬智高一家是何方人氏,历来有多种说法,多个版本辞书说他们出生于今越南高平省广渊,而其地历史上为邕管辖羁糜州治所,所以有说他们是中国人。在中国人的说法中,又有多地称:“侬智高是我们乡里人”,但都未能举证说明,不足为是。中越陆地边境划界才是若干年前的事,追溯到唐宋时代,有些具体事一时难说得清可以理解,但作为侬氏人,祖居“广容之南,邕桂之西”是可以成立的。而农安业却断定:“雁门郡是侬智高一家的出生地”。他的根据还是那本被否定了的侬氏老族谱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历青子名为灿琼公,带下三子增连、增隹、增琪,与兄弟叔侄之子女三千余人迁入维坊市为农及经商……”。农安业即望文生义,无根无据的说:“侬智高爷爷是侬猷,侬猷之父是农增连,农增连一家原来就是雁门农。农增连来到文化发达的山东,也给自己加单人旁”。雁门郡始建于周,及后赵改周制,雁门郡望有童、幸、薄、农、魚、衡、文七氏,史书只记载这些家族有“显赫的背景”,从未见到提及任何个人。几千年过去了,如今雁门郡望居然冒出一个侬猷的父亲农增连来,想必他肯定有比其他家族更高的身份,更特殊的背景,但史书从无记载。农安业也没有任何举证,那本侬氏老族谱也只说增连随着众兄弟一起到潍坊市务农经商,怎么又突然变成了来自雁门郡,而且又成为侬智高爷爷侬猷的父亲,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。至于侬智高爷爷侬猷更离奇,享阳一千五百多岁,但其来龙去脉却无人知晓。话又说回来,侬智高也和常人一样,有自已的爷爷,但他真正的爷爷是谁?中国人说是侬民富,越南人说是侬金德,谁是谁非,我们无法认定。云南侬鼎升先生著文称:“不管侬智高的祖父是侬民富还是侬金德,都是广源州土著民族的首领,而不是那个从未到过广西的叫什么侬猷的汉人”。
侬智高是什么民族成份?农安业说:“他的家庭是汉族地区,他应该是汉族”。他的说法与侬智高一家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记载不符。侬智高的父亲曾任广源州、傥犹州首领和邕州卫职,直至宋宝元二年(1039年)被交址掳杀,其活动范围均在广源州之内,其母阿侬是左江武勒人(今扶绥一带)。侬全福被害后,她带着年幼的侬智高(时年仅为14岁)逃到火雷洞(今大新境),后又逃到云南特磨峒,于1041年与侬厦卿再婚。侬智高本人除了起兵反宋那段时间之外,也从未离开过广源州。农安业所说的“汉族地区”,指的就是雁门郡,这是子虚乌有的事,前面已有说明,不再累述。
雁门郡在山西,非西南边陲的广源州,侬智高一家的祖籍变了,他乡变故乡,民族成分变了,侬人变汉人,还有个生前不曾谋面1500余岁,叫侬猷的爷爷。侬智高在天有知,不知作何感想,是感激还是悲愤?而所有这一切的炮制者,也应该扪心自问,良知何在?
农安业为何如此卖力伪造侬智高家史?用他的话来说,是“为了不授人以柄,不危害对侬智高的重新评价”。一语道破天机,原来侬智高一家并非来自雁门,其民族成分也并非是汉族,只是为了“不授人以柄”和“对侬智高重新评价”,而刻意伪造的。我们不禁要问,人的祖籍和民族成分,为了某种“需要”就可以随意编造的吗?如此人世间还有什么真实、诚信可言?至于“不危害侬智高重新评价”一说,如果不健忘的话,2018年6月,农安业曾著文宣称:千年侬智高冤案即将得到以国家名义纠正,既然如此,还有给侬智高重新评价的必要吗?又有什么别的比国家更高等级,更高权威,给“侬智高重新评价”呢?如果真的如农安业所言,“以国家名义纠正千年侬智高冤案”,我们会拍手称快,但从常识考虑,发生在11世纪宋皇佑年间的事件,由21世纪的当今新中国来“纠正”似乎不太现实。“纠正冤案”之说,恐怕是农安业为一私之念自编自演。如果真的是这样,那他就成为置党和国家声誉而不顾的谎言制造者。
玩弄文字游戏 肆意贬农黑农
贬农、黑农是农安业的秉性。露骨污蔑“农”是“贱意”,农姓是“农奴”,以农为姓“尴尬”、“啼笑皆非”,甚至连农村、农民、农夫、农民工,也被其污蔑为“较含贱意”,在遭到族人遣责之后,不思改悔,而是变换手法,玩弄文字游戏,肆意贬农黑农。农安业说:“侬字强盛和伟大”,而“农字有歧义”。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,是语言的书面形式,我国有几万个汉字,何以独“侬字强盛与伟大”?孙中山被尊为国父,伟大的是孙中山,而不是“孙”字。至于文字歧义的解读,也包含有观点立场。西藏是我国最后的奴隶社会,上层贵族把奴隶当牛作马,任意鞭挞行刑。共产党视百万农奴为阶级兄弟姐妹,中国人民解放军不顾流血牺牲,坚持在雪域高原平息叛乱,推翻奴隶主统治,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人。农安业视农姓为“农奴”、“尴尬”、“啼笑皆非”,而广大农氏族人,爱姓如故,尊祖如一,世代传承,一直到永远。国家设有农业农村部,农字“歧义”叠加,是否要撤销?或者改为“规避岐义”的侬字?变成“侬业侬村部”?
“农改侬是文化意识进步和思想意识进步的表现,不是纯粹改姓问题”,在农安业意识中,农氏家族是文化、思想意识落后的群体,只有改为侬姓才是进步的。改姓是姓氏学的组成部分,包括农、侬在内的中华姓氏,因时因势而改姓时有发生,但利用改姓进行姓氏攻击,农安业可说有史以来第一人,可见其对农氏家族不仅是鄙视,更像是仇视。而事实上,农、侬相互改姓,并非如农安业所说的那样。这里举一个例子:云南省广南县志办侬光兴先生在回答学者访问时说:“广南侬、农姓来源很复杂,主要原因是广南实行土司制度时,这里是侬姓的领地,很多农氏出钱买‘亻’,变为‘侬’姓,1953年土改后,因政治原因,又有侬氏去掉‘亻’旁,改为农姓。但是广南农、侬都是本县人口大姓”。他的这一番话有三个重要含义:一是农、侬相互改姓事出有因。农姓改侬是攀炎附势,‘亻’是用钱买来的,侬姓改农是怕政治牵连。不是农安业所说的“文化和思想意识的进步”;二是农、侬相互改姓,只是少数人的行为,并不影响“广南农、侬都是本县人口大姓”;三是既然农、侬都是广南人口大姓,说明农、侬两个家族是客观存在,不是“农、侬一家”。作为农氏族人,我们了解家族的历史和现状,但无意标榜自己也不想数落他人。我们只是想说:“农落后,侬进步”,并非是事实,也不是广大侬氏族人想说的话,因为这是挑拨农、侬两个家族关系的险恶用心。我们坚信,农安业制造这点阴影遮挡不了具有几千年历史农氏家族的光辉,只有让广大族人更加看清家族异类者的真面目罢了。
“侬是农的灵魂”。农安业这一“金句”,我们百思不得其解。作为文字,农、侬字不同义;作为姓氏,农、侬姓不同名,不同家族属性;作为家族,农、侬两个家族是平等的,侬氏何以成为农氏家族的灵魂?在中华几千年姓氏历史中,一个姓氏成为另一个姓氏,一个家族成为另一个家族的灵魂,从来没有。老师教书育人,被尊为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。何谓“家族灵魂”?这是农安业“研究”出来的又一个“第一”。农姓比侬姓早诞生1300多年,这1300多年无侬姓,农姓岂不就成为“无灵魂”的姓氏了吗?如今农氏家族遍布五湖四海,很多地方只有农姓,无侬姓,根据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各市县编撰的地方志统计,广西有62个市县有农姓记载,全区无侬姓。按照农安业的说法,这些农氏族人岂不就魂不附体了吗?我们读不懂“侬是农灵魂”金句,但知道慌言永远是慌言,也知道阿谀奉承者是什么样的人品。
“历史上本来就是大侬小农”。“历史上”是个笼统的概念,当农氏已是雁门望郡七氏之一时,侬姓尚未诞生。姓氏确有大小之分,但衡量的依据不同,有以政治为标准和人口为标准两种。农安业所说的“大侬小农”不知以什么标准为依据?在奴隶社会,实行“授姓命氏,封士授民”制度。周天子将大大小小奴隶主贵族分封到全国各地进行统治,这些受封的权贵比起无姓无氏的奴隶,他们是大宗。然而“周之宗盟异姓为后”,比起姬姓王族,他们是小宗。在士族门阀盛行时期,姓氏出现了所谓“高门”、“寒门”之分。“高门”、“寒门”之间,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,即所谓“士庶天隔”。“高门”指的是享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特权的显贵之家,他们是“大姓”;“寒门”指的是卑微庶众之家,社会地位低下,他们是“小姓”。这是以政治为标准看待姓氏的大小。这种情况,已成为过去几千年的历史,农安业是否要将历史的车轮倒退到那个年代,用“奴隶主”与“奴隶”,“高门”与“寒门”为标准,作出“大侬小农”的结论?可惜,当时侬氏尚未问世,不知农安业是否具备这方面的历史知识?
以姓氏人口为依据,不带任何政治色彩,这是区分大姓和小姓唯一正确的标准。我国自宋以后各个朝代的《百家姓》,虽然编撰指导思想不尽相同,但都以当时的常用姓为基础进行编排则是相同的。使用频率的高低,基本体现姓氏人口的大小。宋代的《百家姓》收录438个姓氏,其中有农姓,无侬姓;明朝初年,根据当时户部收藏的户口册编成的《皇明千家姓》,收入1968个姓氏,其中有农姓,无侬姓;清代康熙、雍正年间先后编撰两部《百家姓》,也只有农姓,无侬姓。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有关部门多次进行姓氏人口调查,其中有两次以500个姓氏为基准,农姓分别排列在439、478位,侬姓排不上,2018年,由公安部门根据户籍登记,以300个姓氏为基准,农姓排在243位,侬姓亦排不上。农安业所谓的“大侬小农”,不知所持何据?如果尊重事实,农姓人口多于侬姓;如果带着有色眼镜进行意识形态操弄,农姓不仅“小”,且“贱”,但都是不实的污蔑之词。
农、侬两个家族是平等的,谁大谁小,没有讨论的必要。农安业抛出“侬大于农”话题,带有明显贱农辱农和挑拨两个家族之间关系的性质,故而以理以据给他提个醒,冀其长点记性,不要不懂装懂,要学会尊重事实,只凭个人想象和好恶,信口雌黄,既不利于族,也不利于己。
造谣中伤 诬陷好人
打击陷害,恶意诽谤,这是农安业一贯恶习。凡是坚持正义,积极为家族工作的人都是他的攻击对象,不是“贪污敛财,中饱私囊”,就是“反祖排侬”或者是“追名逐利,唯利是图”。但从来未见过他拿出任何事实来举证,纯粹是无中生有,造谣中伤。
从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以来,我们农氏家族有许多族亲,为振兴家族自觉地为家族无私奉献自己的力量,他们不惜牺牲家庭和个人利益,一心一意扑在家族公益事业上,而且做出了显著的成效,受到了广大族人的赞许和拥护。他们追的是家族的名,图的是家族的利,个人只有付出,没有一分一厘收入,捐款要带头,尽可能比别人多,出差有时自掏腰包,几十年如一日,任劳任怨。农安业能做到吗?事实证明,他做不到。前些年他也曾在德保县农氏宗亲联谊会担任顾问,在一班人中强制推行其错误主张,谁反对就打击谁,搞乱了班子,妨碍了家族事务工作正常开展。尤其是当家族出现了意外,需要同心协力,排难解困之时,他始则利用事件挑拨离间,破坏族人之间的团结,未能得逞,继而落井下石,把责任完全推给坚持工作在第一线的族亲;再则怕受连累,怕捐款,他发表声明,退出联谊会。但大名之前还冠以“顾问”头衔,大有卷土重来之意。如今,在广大族人共同努力之下,问题已得到圆满解决,德保几万农氏族人,感激在困难之时伸出援手的族亲,而在他们当中就有被农安业污蔑为“贪污敛财”、“反祖害族”的人。他们比无情无义,半点人情味都没有的农安业要好得多。
农安业为何如此记恨积极为家族服务的人?就其灵魂深处而言,与其根深蒂固的“贱农”思想一脉相承。在他的意识中,农姓人是文化思想落后,没有灵魂,只配做奴隶,令人“尴尬”的群体。一个发展进步的农氏家族是他不愿看到的,因此他将积极为振兴家族努力奋斗的人,当作眼中钉,肉中刺就不足为奇了。另外,这些长期坚持在家族工作第一线的族人,了解族情、族史,是他推行“农侬一家”、“农侬一姓”,难以逾越的“障碍”。所以他对这些人不遗余力,抹黑诽谤,造谣中伤,无情打击,欲置之于死地;再者,他还口出狂言,农氏家族要进行一场彻底的“革命”。由于“革命”不成功,怒火中烧,迁怒于人,发泄私愤。必须严正指出,农安业一而再,再而三,对那些积极为家族服务的族人,进行人身攻击,污蔑陷害,是不能纵容的,其嚣张气焰如果再不收敛,总有一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删除炎帝号
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。他发明耒稆,教民农耕,首创农耕文明,造福于民,有功于世。清《康熙字典》载:“神农,古炎帝号,炎帝教民植谷,故号神农氏,谓神其农业也”。“神农”帝号,与中华5千年文明史共存,与中华14亿子孙同在。如今竟被农安业删除。他写道:“用‘神农’二字太繁,侬就是‘神农’的合成简化式”。
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,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、向心力的内在动力。炎帝号“神农氏”,被改成“侬”,黄帝号“轩辕氏”,不知什么时候,被农安业改成什么东西?事关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儿女的认识和情感。树对立面,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,打棍子,是他的恶习,这次他把自己推上了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,14亿中华儿女的对立面,看他如何收场?
常说“井底蛙”,比喻目光短浅,见识少。而农安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删除炎帝号,又该如何给他量身定位?说他是井底蛙,但井底蛙尚可坐井观天,只是把天看小了而已;说他无知,但他自比鲁班,还端着什么“研究”者的架子;他删除了炎帝号,又高呼“尊神农”,说的一套,做的另一套,所以只能说他是口是心非的两面人。还有“敬智高”也是农安业常挂在嘴边的口号,然而他把侬智高的祖籍、民族都改了。人们常说“魂归故里”,故乡没有了,不知侬智高和他故去的家人,魂归何处?更使侬智高莫名奇妙的是,还给他找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,比他大1500多岁的侬猷做爷爷;他所谓“敬智高”,其实是把侬智高当作自己的护身符,对不同意见动辄把侬智高抬出来,当着棍子来打人,这不是“敬智高”而是害智高。
农安业在无助的困境中,打着古人的旗号,只是为了包装自己,抬高自己的身价。“尊神农”、“敬智高”都是骗人的。